
谢谢师弟小王,今年7月在广州用胶片拍下的一个时刻,太古广场楼上的风很大,阳光刺眼,谈话之中我们似乎都有点人到中年的意思了,事业做到了一个应该改变的时刻,你也收获了人生的新阶段,女儿的降生预示着一个新的轮回,生命的奇特,感怀与捉摸不定的喜和悲,而这些时刻都在经过了好几个月后被我再度揣摩,想一想,7月的广州真是热,是货真价实的溽热,热到没有一丝清透的意味,那个南国的城市既陌生,又熟悉,我在抵达这座城市的第一个早晨,出门去酒店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一盒本地产的牛奶——这已经是我惯常的方式,通过早晨的牛奶去感知这个陌生城市的轮廓。
今年6月回了一次欧洲后,觉得脚步还是不要停下来,虽然不知道最后的目的地在何处,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然后经过了八月,九月,十月,转眼34岁就剩下了最后两个月,我暂时停止了写作,因为更大的理想的驱动,只能暂时放下喜欢的写作,埋头为了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去专注。我离群索居般生活,只保持仅有的固定的同学和好朋友的交流,我有时候会很羡慕以前认识的媒体人,他们飞来飞去,他们在各种派对,时尚的群落中起起落落,但是我的心已转,像是尘埃并未落定前,有一些念想,但也就仅仅是念想。远观的乐趣大于亵玩焉。就不要念及那些浮华,烟火般的兴奋自恋与无法自拔。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轮转,命运自有定数。
说回广州,我还记得夜晚的珠江,有风,跑步而过的人,广州塔发出依据时间不同而变换的色彩,我分别在夜晚的珠江边看广州塔,以及坐在四季酒店的高层,和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喝下午茶,那立在远处的广州塔,在白日里显得现代无比,它象征了一个城市无限生长的可能,但是又是疏离的,充满了一种后现代的奇怪的感觉。广州,被这广州塔分割出清晰的新旧的脉络,放佛是故意划出的界限,让我狐疑。我原来发现有的人注定是你生活的过客,他们只和你发生了最初级的接触而已。我很多时候,为了某些我觉得是朋友的人付出很多,却是热烈之后的冷然,很让我伤心。有的人即便在远方,也可以因为喜好,兴趣的相似走到一起来——这是让人觉得生活原来是因果的一面,也忽然觉得偶尔充满惊喜,不期而遇以及一点点的欢愉。
我在广州,有一个香港的朋友A坐了火车来和我聚会,夜晚点了几道广州的菜式,酒店里的起伏,欲望似乎被疲倦吞噬,举棋不定,并非明白清楚姻缘的线索不能生拉硬套。我一直以来不会去写故事性的小说,因为我觉得各自人生的精彩其实都好过矫揉造作的文字编造。我们忧郁又彷徨,自我又敏感地和这个世界打着若即若离的交道,这本身就是小说——比如,这个香港的A到广州来,我们都情不自已开始用自我的情绪写了小说,我觉得这篇即兴的小说有一个广州的背景,从我住的酒店窗口看到那闪烁的太古广场的巨大商业造型,惶惑中吐露着极大的失落与虚无。
我坐在广州文华东方酒店的餐厅里,我看到对面小区的泳池,骄阳下的蓝,发着光。我似乎能想象出那些嬉戏在泳池中的外国男女的对白,它们和在餐厅中吃食的男女讲的对白毫无联系,它们都淹没在人声鼎沸的城市节奏里。而我在广州的节奏和活动范围极小,显示了一种疲倦和懒散的姿态——包括连续两晚去同一家餐厅吃晚餐,只是换了对象,但是我很开心见到了学电影的两位师妹,和一位师弟。广州的老城,只是师弟开车经过,竟然全部忘记了。被《城市画报》的编辑邀约去做了一次聊天的节目,广州潮流文化的风格,在那幢改造的民国感的楼宇中显得非常好玩又轻松,随后终于去了《城市画报》的办公楼,整个南方报业楼的老楼部分,放佛时光倒流——是好事,我想起了,我初初阅读这本杂志的21岁,或者20的样子,情态,以及对于南国的想象……

今年6月从欧洲回来,我已搬家到了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区域,因为有一个大型的公园,毗邻杜甫草堂,我慢慢喜欢上和这些静物对话,习惯了散步,在夏天看天空的流动,我去看碑拓,读古诗,挖掘更古旧的文字,我觉得它们都有一种灵魂出窍的忧伤,是被冲刷的样子,但是我并非刻意去寻旧,一切都是看到即是的意思,不求甚解。

杜甫草堂里有很多流浪猫,有清晨锻炼的阿姨给他们带吃的,它们都活蹦乱跳,并没有一丝的被遗弃的不高兴。
九月,我回到以前在重庆读书的大学,遇到开学的新生军训,夕阳下那些18岁的背影。我走过自己曾经在十多年前走过的大学校园,去以前住的宿舍看了一眼,但也仅是看了一眼,整个北碚像是另外一个所在。
等待的中午,我走路去了江边,像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这座荒诞而不真实的城市,那江,那阶梯,那小街道上的人影,只是我内心空白,并觉得是想赶紧离开……



这几个月没有写作,偶尔只写一些应景的稿件,觉得我认真写了很多字,得到的回报并非如预期那样热烈,我的内心热烈创作,但新书之于读者冷淡如常(这有很大一部分是出版社的原因),就当是给自己写的字,可以带进记忆里去。也许,命运并非让我停留在这些矫情又世故的文字上,我写我话,旅行的字似乎到了可以说再见的时候,所以我就把这些文字的叙述全部关闭,不过最近还有一本关于猫的散文集,我写了一章设计师王天墨的猫;此外还有一本关于旅行和美食的书,我写了一章关于我在冰岛的旅行——但是等到这些书上市可能还有一些时日。除此之外,我把心从写作中抽了出来,并如萧红写“弃儿”一般心怀厌恶,不想去共鸣,甚至想否定这些已经出版的字。

即便是再用力写,却也是自我的话,简单用“怀才不遇”来归纳似乎也是不公道的说辞,就当是一个生命的插曲。唯一可以抓得住的是,时间敲打,还有两个月,今年就结束了,计划去一次杭州和上海,订好了机票。此外,想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飞回北欧去小住一段时间,我不喜欢熟络,我不喜欢粉饰的那些圈子,我孤独着,也不需要告别的话,我能感觉到刀子在手臂上划出的伤口的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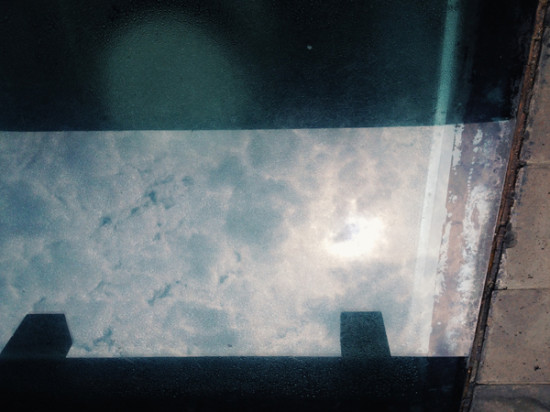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