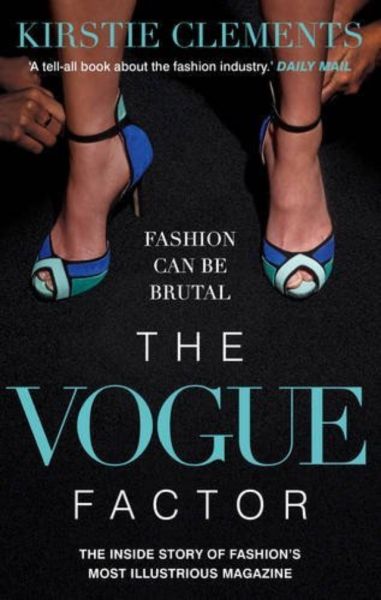
你可能不知道的时尚圈内幕, 从时尚业界到时尚设计师,时装杂志到公关广告,一位业内人士发表真实经历体会,揭示美丽产业背后的丑陋真相,用事实告诉我们不被包养的时装设计师是悲惨的。
众所周知,时装设计一直是烧钱行业,当年时尚小婊香奈儿流落街头之时,如果不是高大威猛的军官从天而降包养了她,现在的女明星、名媛和二奶们在炫耀自己的品味和财富时将会缺少一个极佳选择,而普通男性对于爱马仕的仇恨将会再上一个台阶——感谢香奈儿的存在,让这个世界的炫富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不过话说回来,时尚小婊香奈儿被包养摇身一变成为时尚老婊香奈儿之后还真是张狂呢,各种领域四面开花和包养艺术家,令人瞬间忘记了“那个做帽子起家的乡下女人”香奈儿,也算是时尚界对于包养界的一次反哺了。

直到现在,时装行业被包养的传统也仍然延续了下来,近年来中国设计师风起云涌,不乏打入国际时装周者。尽管我非常不善八卦,仍然不断有好事者凑近我耳边表情神秘地告诉我:这个谁谁,被某个大佬包养了,但也会有某些比较正面的八卦,比如那个谁谁谁,被某个富婆包养了,但也会有某些正面的八卦,比如那个谁谁谁,他家里有钱,给他几百万做衣服就靓玩似的,或者那个谁谁谁,是红三代,你看,时尚圈也并不总是堕落的。迪奥先生和圣罗兰先生,也都是富贵出身,所以穿他们衣服的女人,总少了香奈儿那种苦大仇深气。
但是如果没钱没背景,又不具备被包养条件的人,不如我,如果硬要进入时装行业,也并非毫无可能,只是可能更为曲折和心酸而已。
比如说,你专业学习服装设计四年,毕业出来各种投简历,终于进入某家民营时装公司,从最低层的设计助理开始做起,每天帮总监画几百张设计图,然而他们总是挑出最难看的几款进行加工销售,或许让你把设计图改了几百遍之后成功变成一件极其难看的衣服,他们终于满意了,如此沉浮十年之后你看到了升职的曙光,但也被毁得八九不离十,这时七匹狼或者阿依莲来高薪挖你当设计总监,你也会欣然接受。
或者进入了时尚媒体,成为挑剔事儿的时尚主编手下的一员时尚编辑,在各种非人打压下你终于浴火涅槃,跳槽成为一名八面玲珑的时尚品牌公关,或者吃苦耐劳的摄影造型师。在无数个深夜的酒会或者拍摄结束之后开车返回自己倾十年之力勉强付够首付的70平房子,想到自己飘散在风中的设计师理想,泪流满面,吃一排的脏摊麻辣串也无法慰藉。
这当然都不是我的经历,作为一名中文专业的师范院校毕业生,我仅仅是在我大三寒假开始买书和工具机器,在宿舍里自学剪裁和缝纫,远不具备毕业后进入服装公司的资格——我每次都是把面料披在人台上直接剪裁,看似颇具大师手笔,其实只是因为我不会画画罢了。我甚至痴心妄想索性退学去蓝翔技校学习缝纫,但迫于父母的压力只得作罢。
我是一个勤奋的人,证据在于,我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作出了四十几套服装,并在学弟的倾力帮助下,在学校里办了一个小型的发布会。当时我不惜动用了我最性感的男同学的女朋友的同事,在2007年12月的《新京报》上登出了一小篇新闻,学弟的妈妈也来了,穿着华丽的亮片衣服坐在显特的前排,我出来谢幕时非常惶恐地看到她习惯性的微笑——她一直以为我把她儿子给遮住了,但事实是她发育得还不错的儿子把我给遮住了。事后学弟告诉我:我妈说,小裁缝还挺厉害。发布会之后,为了报答师弟,他去医院割包皮时我陪床伺候。
毕业之后我没有找到任何工作,想靠着做衣服谋生,租了一个小房间,在某宝上开网店接受别人的订单,做衣服,三个月下来做了20来件衣服,赚到大约四五千块钱。那时候不认识任何人,没有对象,没有钱,偶尔约炮,但炮友永远没有包养我的意思,每天吃一包速冻水饺,很害怕,北京奥运会开始了,住在我隔壁的胖子情侣每天都大鱼大肉庆祝中国拿了金牌,他们三十几岁了,还住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吃饭放屁吵架发胖变老。我害怕自己的未来变成这个样子。奥运会结束后,我就生病了。这时远在泰国的同学问我,这里有个教中文的机会,你想过来吗?工资不高,但绝对比北京的工作环境好。我想了想,也许我需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把网店给关了,退了房子,搬回到之前一起住的男生房子里,我告诉他,我只住一个多月。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他白天睡觉,晚上玩游戏,没有性生活。
到了泰国后,时间开始变快。第一年我存了2万元。回到北京半年,很快就花完了。又出去一年,这一年存了4万元。2011年3月,我彻底告别了泰国,回到北京,仍然没有信心做衣服——4万元,在北京能做什么呢?我误打误撞进入了媒体行业,一年之后,进入一本独立杂志《雲爆弹》,成为时尚版和文学版的编辑,我开始和各种品牌公关,各种摄影师,各种模特,各种化妆师打交道,我去了巴黎时装周,去了安特卫普,认识了更多艺术家设计师摄影师。但我知道自己志不在此,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做衣服的。
2014年,我27岁,大学毕业6年。和我同一年毕业的有些同学已经做到年薪百万,部门经理职位,我仍然过着他们眼中不靠谱的生活。也许我已经错过了做衣服做好时机,但我总觉得时间未到——没有钱,没有被包养,没有认识足够的人。
但是什么时机才是最好的时机呢?杂志继续做下去,仍然赚不到钱,我也仍然不会被包养,而认识的人什么时候才算足够?这么等下去,也许一辈子都做不了衣服。我不愿意再等下去。钱不足够,就从少量开始做起,没有人包养,那就算了,认识我的人,如果愿意帮我最好,不认识我不愿意帮我的人,也不必强求。我只需要做衣服,做出来的衣服有人愿意买,能够支撑我继续做下去,就足够了。
2014年1月底,我还在巴黎时装周,刚好杂志出了一些问题,面临做不下去的危机,我赶回北京办离职,相处了两年的同时满目张皇,仓促之下各回各家,抱着东西走在路上,心想,说什么也得开始做衣服了。
中途发生一些波折,有人想买我们杂志团队,继续做这本杂志,中间曲曲折折误了一两个月,左后感觉还是不靠谱,这事不了了之。五月底,买好了需要的布料,把放在箱子里跟着我东奔西跑了六年的机器搬出来,开始做衣服。同时康阳自己做了“公路商店”网站,可以把我的衣服放在上面出售,样子门面做得很足,大家都在自谋出路,不如抱团取暖,互相帮衬。
刚开始只是练手——毕竟六年没做,虽然有坚持,但不知道自己的手艺是否还在。而第一个系列到底要做什么,也是很挣扎的一个过程。这六年积攒了太多想法,想要一下全部做出来,显然是不现实。刚好买到一块东方印花的面料,左思右想,最终还是先做一个东方系列。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是“寻根”,但不装逼的事实是,东方样式的时装最好做,缝线少,宽松简易,也好穿,适合我现在的水平。这几年元气伤得有些厉害,想要慢慢恢复起来,不敢急切。
但各种事情接踵而来。杂志还是要继续做下去,而且决定七月去安特卫普做新一期内容。时间紧迫,我快速地赶制出几款样衣,把面料送去制版加工,就匆匆带着杂志的一班人马飞去比利时。在欧洲的十天里,每一天都想着衣服。那几天飞机纷纷往下掉。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自己回不来北京了,半梦半醒间说了梦话,问屋里的同时:我们还能回去吗?我的衣服haunted没做完呢。现在想来当然是啼笑皆非。
回来之后衣服做出来一部分,我又继续赶出一部分样衣,希望能在夏天过去之前完工——再也就卖不掉了。自己的存款全都搭进去了,想起来感觉轻飘飘,怕不能回本,我妈还指着我养老。这辈子总是觉得欠她,什么也不能随她愿。夜里失眠,这种恐惧也是不能跟人说的。
好在衣服总算出来了,虽然还是不是很满意,但硬着头皮也要上,不断给自己打气:你用好的面料,做工也比市面上的衣服要精细,风格也有,不用担心,一定会有人买的。当然还是失眠,死活睡不着的时候,猛灌一瓶酒到头就睡。每天起来仍然是笑吟吟的,跟谁都挺好。但是一遇事就着急,沉着脸说话。自己也知道不好,但控制不住。我想我还是太紧张了。
做完衣服要拍照,我觉得不能找职业模特——毕竟衣服是给普通人穿的,要让大家相信,普通人也可以把我的衣服穿出效果。于是找了十来个普通女孩男孩,穿着我的衣服在摄影棚里拍摄。配上妆容,发型,看着镜头的非职业模特们,我的信心也渐渐的回来了。请不起摄影师,适应也是我自己来。付完所有的拍摄费用,身上几乎已经清空。也许真的把自己逼到绝路了。还得再继续往前努一努,死也要死得好看一些。
这篇文章并非关于理想。确实我一直羞怯于谈论理想。总觉得这个词已经被谈论得太多,不管是放在这个时代,还是放在自己身上,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再大的理想归根到底也无非出名,赚钱。但我的理想其实只是在美国一个乡下农场里,白天干活,养鸡喂牛,晚上写写小说,有一个国内的贪官男朋友,每隔一两个月飞来美国看我。一点儿也不高尚,但是我觉得挺好。我的理想跟做衣服没有太大关系。做衣服更像是我身体里源源不断分泌出来的某种激素,堆积在身体里让我难受,我需要把它排出来。而我一直最看重的写作,我反而从来不急。
有人曾经问我,你打算一直做衣服,把它当成一生的事业吗?我回答说,我不确定,也许做两三年就做不下去了,没有足够的人买衣服,没有前继续做下去,也许能做到十年,二十年,做残了再也做不出新的东西,就像我最喜欢的设计师Vionnent那样,避世不出。她是和香奈儿同时代的设计师,是个划时代的设计天才,在1939年,她关闭了自己所有的服装店,从此和名利场避世而不见,直至1957年离世。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